鼠年大年初一,我做了一道鸡汤泡炒米。15岁的大女儿莞莞有些不屑地说,新年的早餐,就吃这个?我说,你不要看不上眼,这可是我家乡有名的美食啊。

我没有骗她,鸡汤泡炒米,真的是我老家枞阳乡下过年时的一道招牌菜。我小时候,家中生活十分困难,但无论怎么困难,大年初一的早上,一碗鸡汤泡炒米,还是少不了的,没有了它,似乎就没有过年的样式了。
据说炒米是中国最早的快餐,其前身是灾民难民逃荒时的干粮。明朝初期,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各地区经济,朱元璋决定对江淮地区进行移民,大量江西老表迁入安庆,他们将生米炒熟之后带在身边充饥,这种不易变质的食品就成为了路途中最简便的干粮。安庆作为安徽曾经的首府,聚集了大量的移民,炒米就此流传开来。而用鸡汤泡炒米,则是安庆人的智慧了。
鸡汤泡炒米,看似简单,但做起来一点也不简单。我小时候,母亲做鸡汤泡炒米,食材和火候都是很有讲究的。
腊月二十边上的一天早晨,母亲很早就起来,在灶膛里架起木柴,用大铁锅烧开水,那时候乡下使用的都是土灶,灶膛很空,铁锅很大。水就要烧开时,母亲找出木盆,“哗”一下,将蛇皮袋里的糯米倒出来,足有半盆,这些糯米都是事先筛过的上好的糯米。母亲用葫芦瓢将铁锅里滚烫的开水舀进盆里,一直舀到开水高出米面三四公分。浸泡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不能长了,长了,米粒全泡化了,会沾在一起,成了一个粑粑,炒不起来;也不能短了,短了,米粒没有浸泡透,炒出来的米硬心,嚼不动。我记忆里是要泡一上午的,中间还要换一次开水,直到糯米粒颗颗胀透到松软,用手一捏刚好能摊成薄片。吃过午饭,母亲将盆里的热水倒去,加入冷水冲洗几次,防止米粒粘连。然后,捞起,盛放在筛子或簸箕上沥着,直到沥干沥透。若是遇上上冻的日子,就更好了,据说炒出来的米会更香。
炒米多在腊月二十四日,过小年的日子。吃过早饭,差不多家家户户就开始炒米了,很快,炒米的香味就在整个村庄漾开了。
母亲在灶膛里架好干木柴,将大铁锅烧热,在锅底倒入一点菜油,用竹帚(竹枝扎成扫帚形状的小竹把)将香油沿锅面刷一圈,待菜油滚热冒出烟雾后,舀一碗米倒入锅里,用竹帚不停地翻炒。在大火的作用下,米粒在锅里跳着蹦着,宛如一场精彩的舞蹈比赛,空气中很快就传来了米粒的香气。柴火在灶膛里噼里啪啦地响着,米粒在锅里噼里啪啦地跳着,一幅壮观热烈又喜庆的画面。直至米粒在锅中呈现浅浅的焦黄色,才算是炒熟了。母亲快速地放下竹帚,抄起锅铲将已微黄的炒米起锅上来,放进脸盆里,接着炒另一碗。

那时候家中孩子多,母亲每年都会炒上一个上午。我们经常吃着炒米就算是午饭了。这样炒出来的米,脆、香,有嚼劲,除了泡鸡汤,还可当零食来吃。炒出来的米,凉下来后,才盛入坛子里加盖密封起来,以免回潮。
老母鸡常常是在大年三十的下午才抓来宰杀的。鸡汤泡炒米用的老母鸡,一定要现杀,不能用老早就杀好的陈鸡,那样炖出来的鸡汤有很重的腥气。也多用隔年的老母鸡,不能太老,太老了的母鸡,肉柴,嚼不烂;也不能是当年的母鸡,当年的母鸡,肉太嫩,炖不出浓郁的香味;更不能用公鸡,因为公鸡的肉质细腻,炖出来的汤少有鲜味,显得清汤寡水的。
母亲杀鸡的时候,嘴里会念念有词:“小鸡小鸡你别怪,你本是人间一道菜。脱了毛衣换布衣,糠箩跳到米箩里。”这只老母鸡跟随母亲两年,多是会下蛋的,是母亲一直有意留着的。母亲亲手去宰杀它,心里自会有许多不舍与难过。
母亲将杀好的鸡洗净切块,放进一只大瓦罐里,洒上盐、姜片等佐料,先放在一边,忙着准备年夜饭去了。一直等到年夜饭准备完毕,要开席了,母亲这时才将瓦罐拿过来,倒上开水,合好盖,将瓦罐放进灶膛未燃尽的柴火里煨着。乡下熬鸡汤,很少炖,多是这样煨出来的,这也许是因为,炖食物,既浪费柴火,又难控制火势大小,相较而言,煨就简单多了,还让鸡汤多了几分地道的烟火味。一直煨到大年初一的早上。除夕的夜里,若是半夜醒来,便觉得满屋子都浸润在鸡汤的香气里,诱得人饥肠辘辘,无法重新入眠,这对当时年少的我,实在是一种折磨。
大年初一早晨,我很早就会在迎新的鞭炮声中醒来,穿上新衣,出门和小伙伴们一起,挨家挨户去捡没有炸响的鞭炮。我们比赛似的,看谁捡得更多,然后将鞭炮用力往地上甩,或是用石头砸,听着“砰”的一声,小伙伴们都笑了,笑声成了迎新的第一道曙光。遇上雨天雪天,新衣服一会儿就拖泥带水了,人有时也成了“泥人”,但我们也不管不顾,直到我们母亲的喊叫声穿越半个村庄钻进我们的耳朵,我们才会恋恋不舍地告别小伙伴们,各自回家吃早饭去了。
我每次回到家中,看见每人面前的碗里都已盛放了半碗炒米,盛满鸡汤的瓦罐摆放在桌子中央。待我们坐定,父亲便会揭开瓦罐,给我们每人的碗里舀两勺滚烫的鸡汤,霎时,“滋滋”声响起,热雾袅袅升腾,香气直钻鼻孔,心尖上便有一群小蚂蚁爬过。我迫不及待轻抿一口热汤,在鸡汤的香味揉合着炒米的香气的浸润下,满嘴的味蕾一时间欢呼雀跃起来,吸几粒炒米,轻轻咀嚼着品尝着炒米的脆酥味,每喝一口,我都忍不住舔一下嘴唇。我喜欢先把鸡汤喝完,剩下的那些炒米完全瘫在碗底,抱作一起,柔软得像一团浓浓的蜂蜜。这时用筷子一划拉,全部收入嘴里,那种香甜和满足直抵心底,让人会不由自主地伸个懒腰,吁口长气。我那时候想,所谓山珍海味,大抵也不过如此吧。

瓦罐里剩下的鸡汤,便不舍得吃再了,母亲会小心存放着,待正月里来亲戚时,端上一碗鸡汤泡炒米,算是一顿简单而又不失礼节的招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后,春节就少回家去,也就很少再吃到故乡的鸡汤泡炒米了。现在生活好了,鸡汤泡炒米也不再是珍馐了,但仍然算得上是一道佳肴,每年春节前,有老家的亲戚朋友来看我,常会带一只老母鸡给我,说让我过年鸡汤泡炒米吃。我偶尔也会做一次,但不知怎么的,我再也吃不出家乡的鸡汤泡炒米的味道了。
只是这些年来,故乡鸡汤泡炒米的味道一直留存在记忆深处,偶尔想起,那特有的香气便会在心底漾起涟漪。今夜,当我坐在电脑前,敲打这篇文字时,四周一片寂静,寒风裹着冷意从阳台吹来,我仿佛又闻到了故乡鸡汤泡炒米的香味,我不由自主地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用手指抹了抹嘴角流下的口水,伸了伸懒腰。我知道,人生在世,有些岁月远去了,便无法回头也无可挽留,但总会有一些记忆,一如故乡的鸡汤泡炒米,温暖甜蜜芬芳着未来的每一片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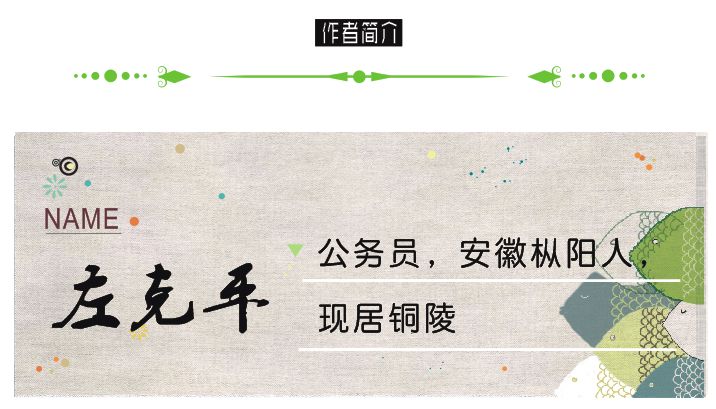
|
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
编辑: 蒋骁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