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铜做成水稻的样子
——王汉英散文集《一条大河波浪宽》序言
许春樵
大江边的王汉英提起笔,她的视线里江水浩荡,江风猎猎,白帆点点,岸边的芦苇在她的笔下由青变黄,“一网鱼虾一网粮”的黄梅调从姹紫嫣红一直唱到大雪纷飞。江边是王汉英散文的地理背景,也是她散文的精神故乡。
“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轻帆挂与白云来,棹击中流天倒开”,洋洋洒洒千百年,长江流淌着水,也流淌着诗,大江边的王汉英写诗,也以诗的眼光观察和纪录她生命中的风土人情、田园风光、人文历史。
诗意情怀,诗性叙事,这是王汉英写作的基本姿势,也是其极具个人化的文学标签。
写作写的都是作家的“个人自传”,这一判断足以成立的理由是,作家在作品中即使不写个人生活、个人经历,但个人看待现实、历史、情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注定了要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就像你打开一瓶酒,看不到酒精,酒精在无形空气中已暴露无遗。
文艺批评学中的“作家自传”是指“精神自传”。
王汉英渗透进散文写作中的精神指向究竟是什么,读完这本集子,明确感受到诗意的人生态度在诗性的文学表达中闪耀出人性的光芒。
王汉英在《青铜器》里泄露了天机,她不喜欢远古青铜器“凛寒,权威,不温暖”的沉重;她“喜欢‘轻’,比如轻音乐,轻抒情,‘轻’的东西,拿得起,放得下。不影响吃饭,不影响正业”。这不是视觉选择,也不是感觉嗜好,这是人生态度的选择,是生活立场的定位。“轻”是心灵世界的轻松、自由、率真、随性的精神体验,而不是物质世界的分量大小和数量多寡。
这本书中的王汉英是唱着戏文、听着音乐、闻着芬芳长大的,她的散文没有抱怨,没有苦难,没有伤感,更没有愤怒与敌意的文字干扰和影响到她欣赏《追鱼》、《与主更亲近》、《渔光曲》的心情。当年米卢调教中国男足时,说“态度决定一切”,你有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生活,王阳明的“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王汉英笔下贫穷的年代,尴尬的处境,挫折的人生,被她整合出了月白风清、春和景明的诗意来,十五岁的王汉英在《十六铺》差点遭遇拐卖,那个令人心惊肉跳的经历居然写得平静而温暖,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上海佬”保护了懵懂而无助的少女,于是“人人都说上海话难懂,我觉得格外适合我的耳朵”,“我一开口说话,上海就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不说话的时候,我跟上海是一体的。”精准的感觉描写直击人心。《二度梅》里的“杨镲”是一个被流言搅碎了的乡村女艺人,王汉英却写出了女艺人在压抑和嫉妒的的疼痛中“以野火的姿态燃烧”,作家以宽容的态度,以仁爱之心,为人性开脱和辩护。《追鱼》中书生张珍和真假“牡丹”的悲情故事,王汉英没有进行道德裁决,而是醉心于“人鱼恋”的浪漫和传奇,当神话照亮另一出丹姑娘现实悲剧后,最后落笔于敢爱敢恨的精神旨归中“换一个自由自在身”,走向“另一番圆满”,“真是慈悲”是王汉英内心深处隐秘的理想主义生命意识。
如果你以诗意的情怀去抒写生活,生活就是一首诗。
《江湾何年》、《磨剪子——抢菜刀》、《留声机》等篇章的乡村记忆里,平静得近乎贫瘠的乡村弥漫着田园的诗意和豁达乐观的生活气息与生命光辉,《江湾何年》是一首唯美主义的田园牧歌,也像一幅浓妆淡抹的水墨丹青,“天边的残月即将完全融入云层里,乳白色的薄雾从江面向江滩乱石堆飘去,蔓延至石堆后浩荡的芦苇,使这些植物变得湿漉漉的。一两条因搁浅而枯槁的小船散落在芦苇的附近,船板上沾着雾气水珠,几株杂草从船舱的缝隙里开出白色小花。再向前一步,雾气就触到密密匝匝的杨树林了。雾气尚未涌到杨树林,江湾村的鸡叫了,光线越来越亮,幽蓝色的天空向淡青色过渡。”汉字的偏旁部首,在王汉英的艺术想象中,全都幻化成笔墨纸砚,先作画,后成诗。
如果说《江湾何年》是一幅水墨画,《磨剪子——抢菜刀》、《老味道》就是两幅民俗风情画,如同天津杨柳青年画,亦如陕北剪纸,土味、韵味、滋味彼此渲染,相互成就,是今生的记忆,是来世的乡愁。“要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隔几分钟,便剥开糖纸,先吮吸一下,再小小的咬上一口——直甜。那甜啊,一直甜到现在。”王汉英在老旧的时光里,打捞出新鲜的声音,在有限的生活空间里,还原出无限的童年乐趣。王汉英的生活辞典里没有收入“黄连”这一词条,这不是无意疏忽,而是有意放弃。
王汉英散文很是迷恋戏和音乐,还有音乐的节奏与调性。音乐是诗性形而下的打开,《渔光曲》、《锁麟囊》、《山鸣谷应》等将戏曲、音乐以及节奏细腻描摹,描出的是艺术趣味,是人生感悟,是情感体验,听着戏,唱着曲,哼着歌,像音乐一样地活着,人生就被谱写成了美妙动人的旋律。“山鸣”是大山在歌唱,“谷应”主部音乐的和声,有如此独特的感觉,诗意的人生中,生活就是一首歌。“小提琴的头开得太好,像独白,轻轻的。循着独白,小提琴的调自低而高,似海浪一波波地荡开来。太阳从海面升起,光芒斜照海滩。”“一个人在光阴里听戏,像是忽然明白了母亲。”
书中的文化散文占据相当篇幅,《振风塔》、《呈坎》、《屯溪老街》、《安徽的母语》以及桐城派《棹击中流天倒开》等三篇,鲜明的个人特点表现为历史梳理、文化思考中的诗人视角、诗性叙事。
在相当多的文化散文中,有文化,没文学;有文学冲动,没有文学格调,更缺乏诗意。王汉英的文化散文是以文学的诗意去观照文化和历史,而不是在学究式的文化呓语和历史考据中再涂抹一些勉为其难的文学颜料。这是王汉英与其他文化散文写作的一个界限,也成了一道鸿沟。屯溪老街“把建筑让给天空,正是黄宾虹画中的留白,深墨的地方是一座老桥,而留白的地方,正是徽州人内心的天空。”在黄宾虹的笔墨和线条里体验的徽州老街,老街的历史就不再重要了,老街在诗性的天空俨然是一幅画。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个桐城派夫子在王汉英笔下灵动飘逸,出神入化,“方苞回到村庄,像月光回到大地。”“刘大櫆的地理审美,目光从江北到了江南,”而姚鼐的生命意识、归来意识、美学意识,支撑点是归来,姚鼐辞官隐逸书院,是精神云游、灵魂还乡,美学意识由此而被酝酿和发酵,生命意识最终定型。这是与世俗人生公然对抗下的选择,是生命诗意的必由之路。
王汉英把复杂生活的简单化,将困厄的情境诗意化,这里除了生活态度之外,还有一个强力支撑应该是来自于她强大的诗性叙事能力。文学是通过语言和阅读进行对接的,日常化的白描和传统叙事的惰性旷日持久地销蚀着人们对文字的热情和欲望,远离现代审美的文字缺少张力,同时也严重降低着阅读趣味。王汉英的散文语言是诗性的语言,是被内心过滤过和被情感体验过的语言,是现代性的文学语言。“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来的声音。”听到下雨,是心理感觉,从声音里感受到风卷起来了,这是通感,不是白描。“夕阳落入长江的远处,暮色开始从长着芦苇的天空浮出来,街铺上传来木板门,一扇扇合到一起的声音,舀水的声音,万块磕碰的声音,江风的声音,旅人匆匆赶路的声音.......黄昏的声音。”前两句是看到的景象,后面是听到的景象,是心理经验,而不是视觉纪实,最后一句“黄昏的声音”是感觉体验后的理性定位。“春节一走,丢给女人春夏秋冬”,这里是物理上的时间,心理上的空间,寥寥两句,将留守女人“孤独的境界”彻底抖开,也是王汉英所关注的朱光潜先生“移情说”的具体实证,“移情说”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是“有我之境”,即环境“着我之色彩”,西方叙事中的通感、异质比喻、隐喻、象征、超验叙事都属于“移情”艺术范畴。王汉英语言的跳跃、间隔、留白、中断的语言结构,是“诗性叙事”的基本节奏,而且实现了自由熟练的操控。这也是王汉英个性叙事的一个显著的优势。
散文跟读者之间,首先是语言对接,其次是信息交流,最后是认知的共鸣,也就是思想和情感同频共振,这当是文学的终极价值所在。王汉英散文是诗性的,是充满诗意的,但王汉英散文最重要的价值是提供了一种和现实世界如何相处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立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但可以承受之轻,不与生活较劲,是潇洒,是浪漫,是诗意,“生命到了某些时候,是要学着往回收的,回归到内心的清简。”
书中的一个标题,对此作了形象而准确的注解:把铜做成水稻的样子。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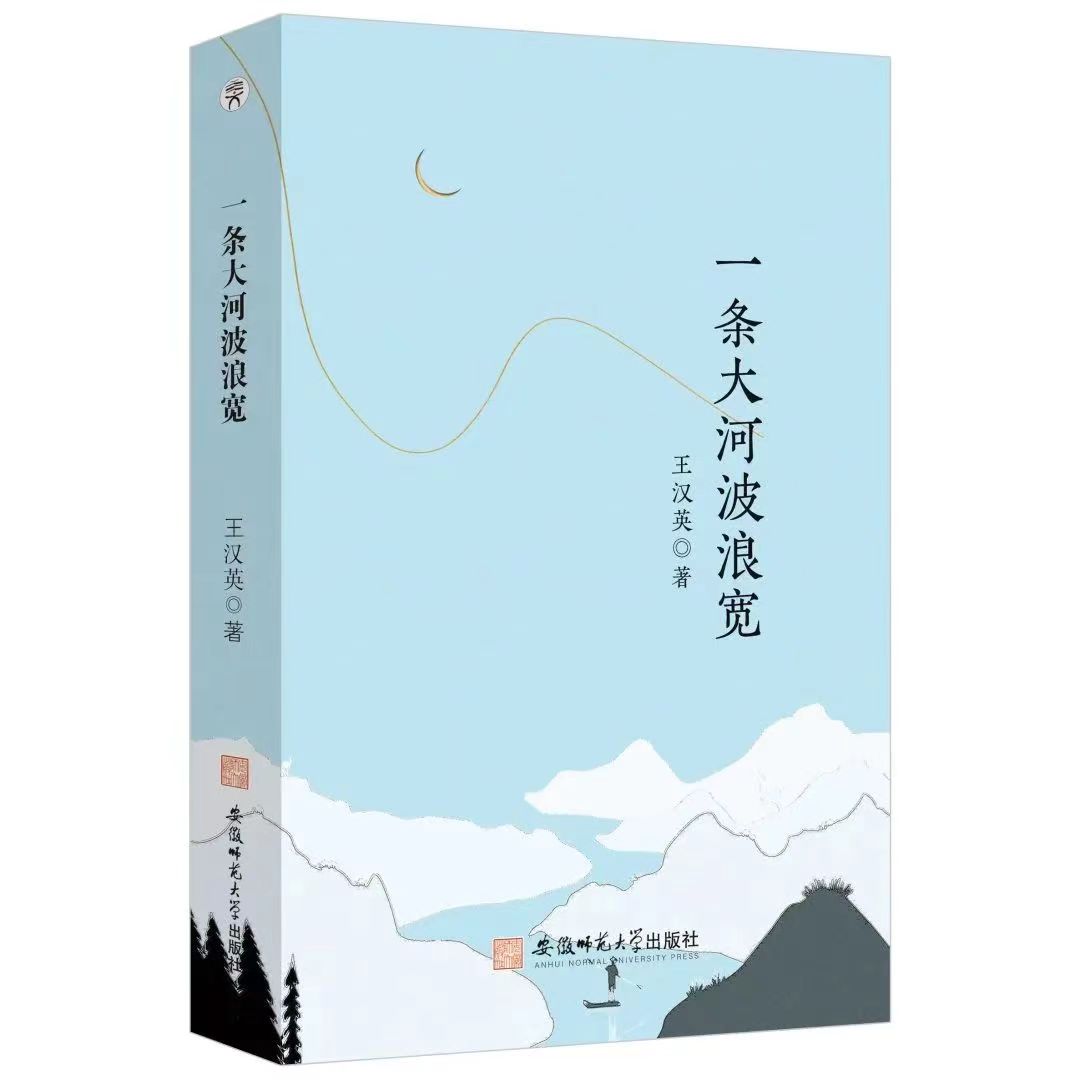
(许春樵,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安徽省作协主席,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来源:芜湖日报
|
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
编辑: 蒋骁飞
|









